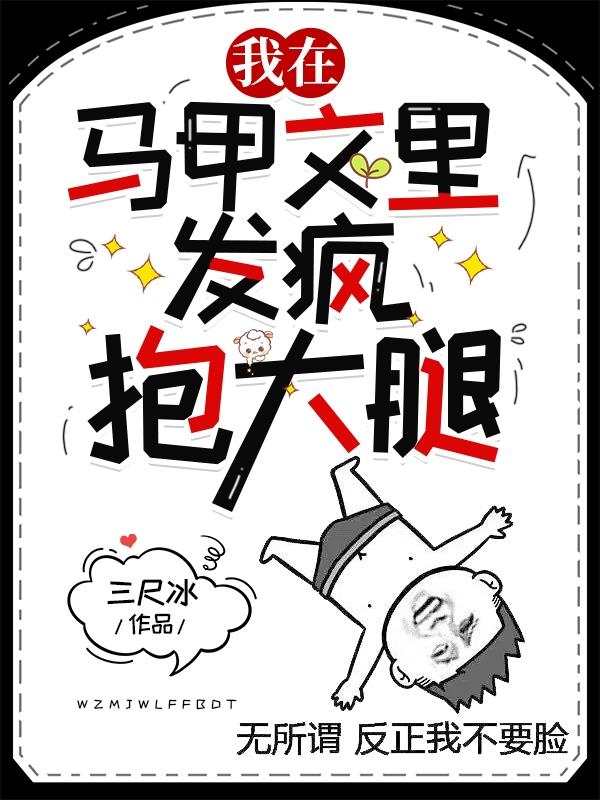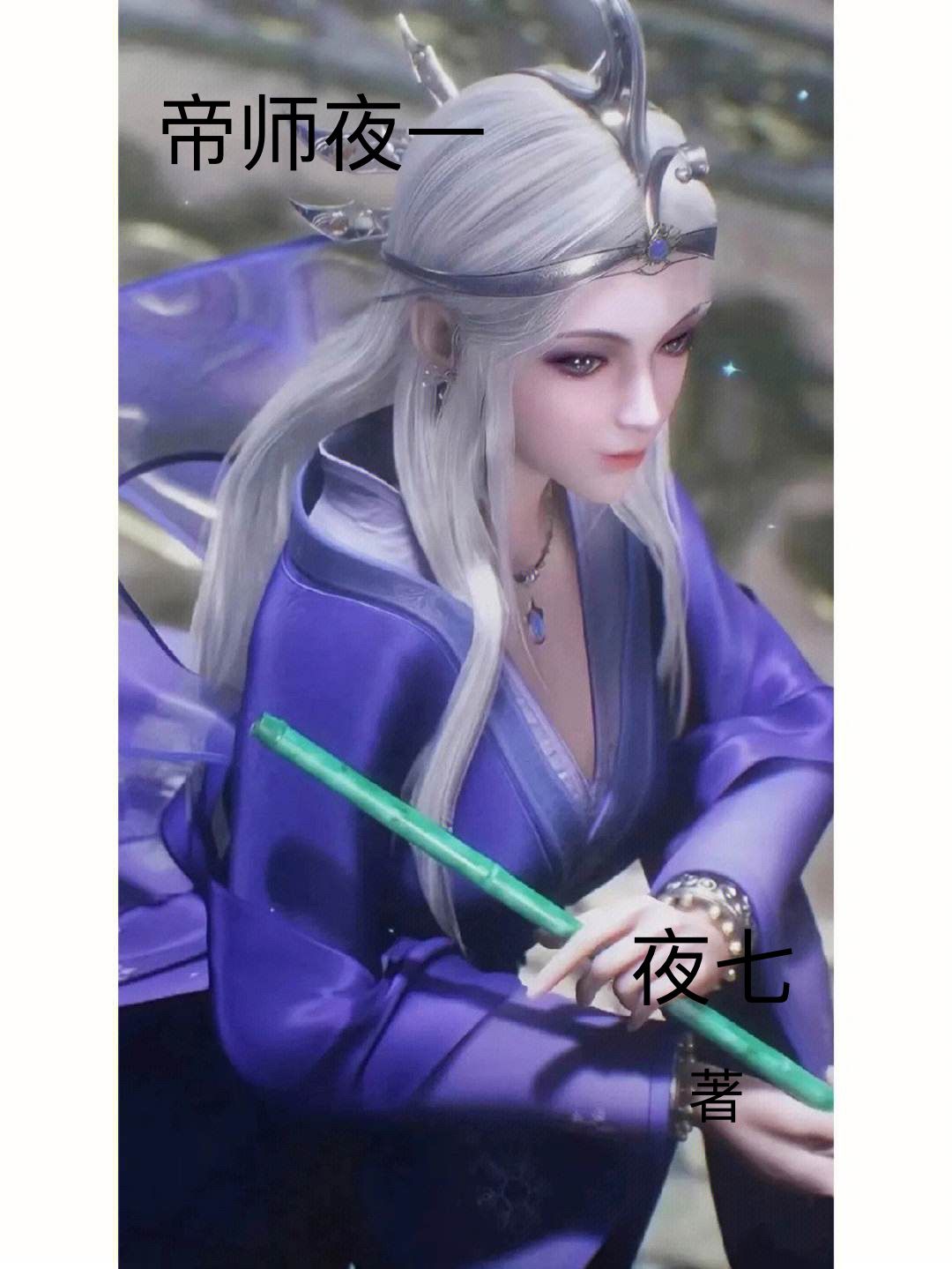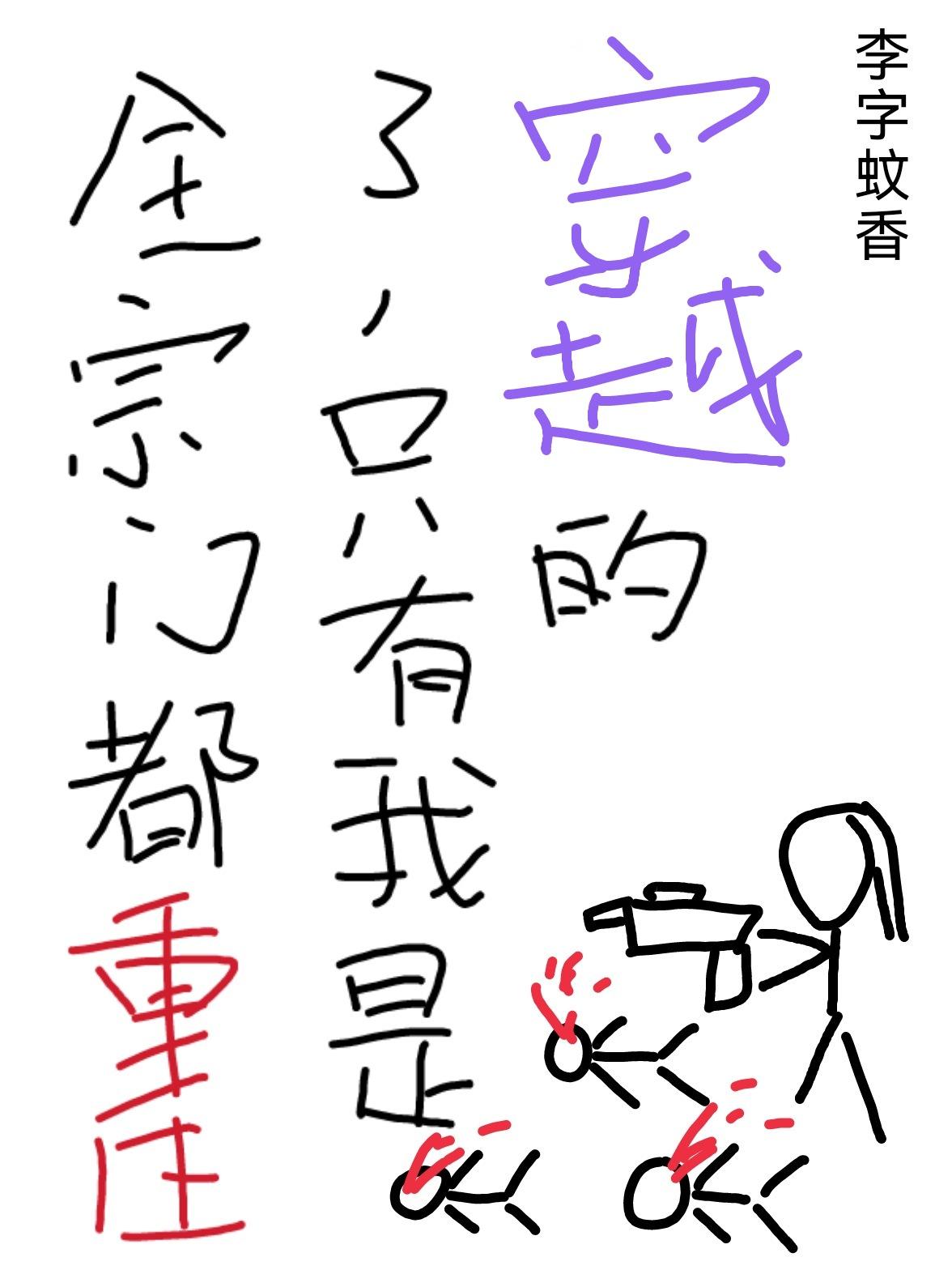1998年夏末,我握着祖母临终前塞给我的黄铜钥匙回到河北老宅时,屋檐下的蛛网正被斜阳染成血红色。钥匙插入斑驳铜锁的刹那,檐角风铃突然无风自动,惊得我险些摔了怀里泛着霉味的雕花木匣。木匣里躺着三本蓝布封皮的线装笔记,最上层那本扉页赫然写着”丁酉年冬月廿三,见保家蛇于李宅”。我认得这是祖母的笔迹,她生前总爱用自制槐树汁墨水写字,此刻那些深褐字迹在暮色中泛着诡异的光。第二日清晨,我循着笔记指引找到李老太太的旧宅。坍塌的院墙后,疯长的野蒿足有半人高,唯独当年大姑描述过的柴火垛位置寸草不生。当我用树枝拨开浮土,指尖突然触到某种冰凉滑腻的物体——是张完整的蛇蜕,三指宽处还沾着暗红血迹。“这宅子不能进。”身后传来的沙哑嗓音惊得我跌坐在地。转身看见个穿藏青布褂的老汉,他浑浊的右眼蒙着白翳,左手缺了三根手指,“七三年修水库炸山,震塌了蛇仙洞,那窝青鳞蛇就搬来李婆子家。“他残缺的手指点着蛇蜕上的血迹,“看见这朱砂印没?保家蛇认过主的。”老汉自称是当年水库爆破队的,他说李老太太独子根本没去南方打工。1975年清明夜,暴雨冲垮了后山坟地,有人看见李家长子举着招魂幡在泥石流
暴风中文 通过搜索各大小说站为您自动抓取各类小说的最快更新供您阅读!
暴风中文 > 青鳞志最新章节列表
推荐阅读: 农门炮灰:全家听我谐音改剧情、 造化长生:我于人间叩仙门、 隐藏在霍格沃兹的占卜家、 欢迎来到成神之旅、 夫人她马甲又轰动全城了乔念叶妄川、 溯灵圣体:林洛的复仇之路、 爱上和尚、 新婚夜,病秧子老公求我亲亲他、 魔极道、 初遇心上人、 我老婆竟然从北源区来找我了、 书画学院的修仙日常、 读痞幼的书、 快穿之夏姬、 家有表姐太傲娇、
- 三尺冰我在马甲文里抱大腿发疯
- 1998年夏末,我握着祖母临终前塞给我的黄铜钥匙回到河北老宅时,屋檐下的蛛网正被斜阳染成血红色。钥匙...
- 梅菲斯特1871穿越在盘龙之玉兰元年
- 1998年夏末,我握着祖母临终前塞给我的黄铜钥匙回到河北老宅时,屋檐下的蛛网正被斜阳染成血红色。钥匙...
- 李字蚊香你惹她干嘛?她宗门宠她如命
- 1998年夏末,我握着祖母临终前塞给我的黄铜钥匙回到河北老宅时,屋檐下的蛛网正被斜阳染成血红色。钥匙...
暴风中文推荐阅读:灭世魔头又如何、 快穿:老婆每次都又美又惨、 上帝狠宠作精,主角被逼黑化、 恶女当道!我才是真正的爽文女主、 穿成虐文拖油瓶,靠发癫搞崩剧情、 惊悚:我的攻略对象都很恐怖?、 女县令、 男主绝嗣!不怕,宿主她好孕多胎、 综影视:解我意难平、 山君家的山头是座珍宝库、 求娶敌国小侯爷、 迷雾哀牢山、 月光与云霞、 拨云窥日【刑侦】、 当宠后是个体力活、 快穿,绝嗣男主有后了、 重生:冷艳女王甜蜜复仇、 我在无限游戏里和疯批恋爱、 港综:每日新情报,从烂仔到首富、 刑侦之死亡真相、 旗有辞礼、 我被师娘抢去了魔女山、 和闺蜜一起穿到冷宫后,我躺赢了、 快穿:男主黑化了你不知道吗?、 举报!她在直播间造原子弹、 四合院:悟性逆天?技能无一不精、 命定伴侣回归:反派你先别黑化、 农女逍遥、 我做男仆的那些日子、 从帝骑开始的破坏者、 丝芭之这个女人我见过、 谋家、 跨越盛夏遇见你、 谢谢你,让我相信爱情!、 清穿之在康熙后宫当送子娘娘、 诡异降临,我的男友非人类、 嫁世叔、 凉薄不过女人心、 我在快穿世界,专治各种不服、 快穿绝嗣帝王娇宠命定好孕小娇妻、 豪门继承人马甲太牢,扒不动、 武炼八荒之天地捞尸人、 明日方舟:赛博之影、 穿越港综当警察但系统不对劲、 快穿系统:炮灰反派美又撩、 七零军婚,大佬携侯府在农村基建、 燃烧少女的夏天、 韶华仙踪、 看了又看之无限惊悚、 转生:逐步登顶成为蛇神、
暴风中文搜藏榜:农门炮灰:全家听我谐音改剧情、 造化长生:我于人间叩仙门、 隐藏在霍格沃兹的占卜家、 欢迎来到成神之旅、 夫人她马甲又轰动全城了乔念叶妄川、 溯灵圣体:林洛的复仇之路、 爱上和尚、 新婚夜,病秧子老公求我亲亲他、 魔极道、 初遇心上人、 我老婆竟然从北源区来找我了、 书画学院的修仙日常、 读痞幼的书、 快穿之夏姬、 家有表姐太傲娇、 参加摆摊综艺后肥姐成了顶流、 凶案真相、 我在八零建门派、 小师祖在炮灰宗门大力投资、 被赶出家门后,真千金疯狂掉马甲、 被当替身,踹渣男后闪婚千亿大佬、 荒年悍妻:重生夫君想要我的命、 创世幻神录、 贺年有礼、 傅总的小娇妻又甜又软、 假死后,彪悍农女拐个猎户生崽崽、 快穿: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、 废妃无双、 这个实教不对劲、 国密局都来了,还说自己不会抓鬼、 开局被甩,转身带崽闪婚千亿总裁、 仙途传奇:修仙家族、 郡主扛着狙击杀来了、 汪瑶修真传、 四合院:许大茂的新生、 夺舍圣主的我穿越到了小马宝莉、 乡野村姑一步步算计太傅白月光、 仙子师尊的掌控欲实在是太强了、 暴徒宇智波,开局拜师纲手、 诸天从噬灵魔开始、 龙族再起、 气运之子别慌宿主她好孕又多胎、 仙妻太迷人,醋夫神君心好累、 我的二次元之旅,启程了、 赛尔:没有系统的我,点满了科技、 修真界亲传们没一个正常人、 春历元年、 女尊:昏庸女帝的阶下囚、 满分绿茶满分嗲精满分作、 凌虚之上、